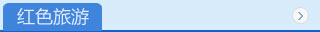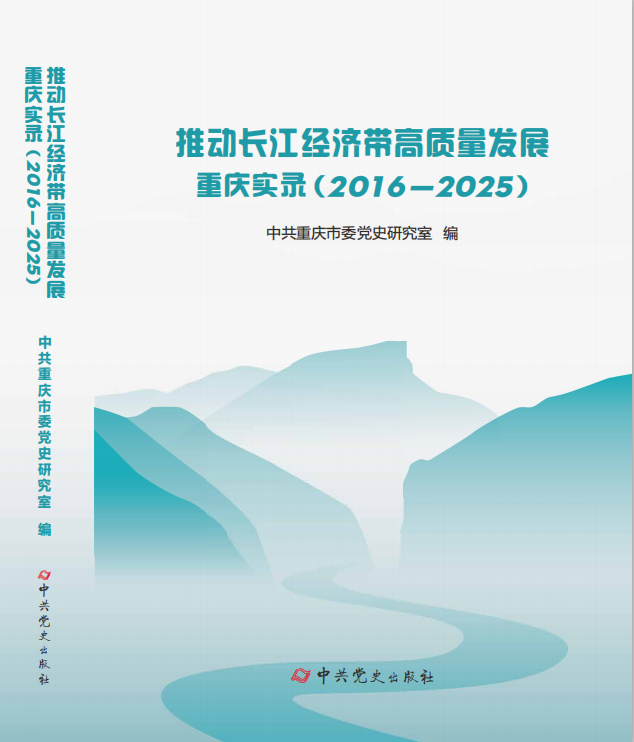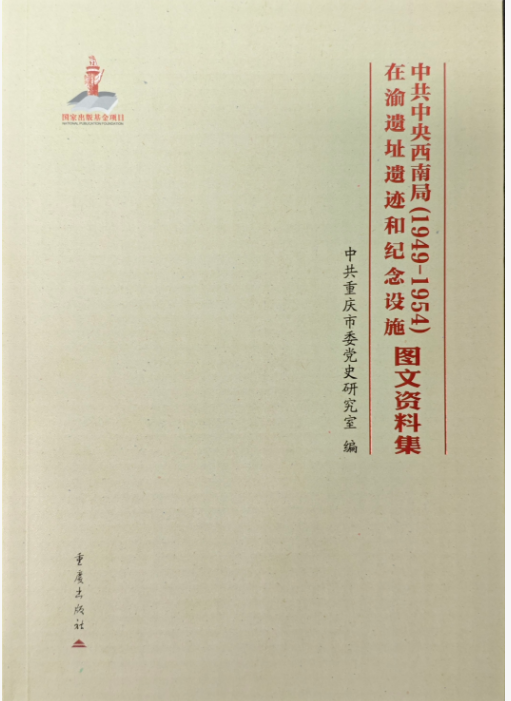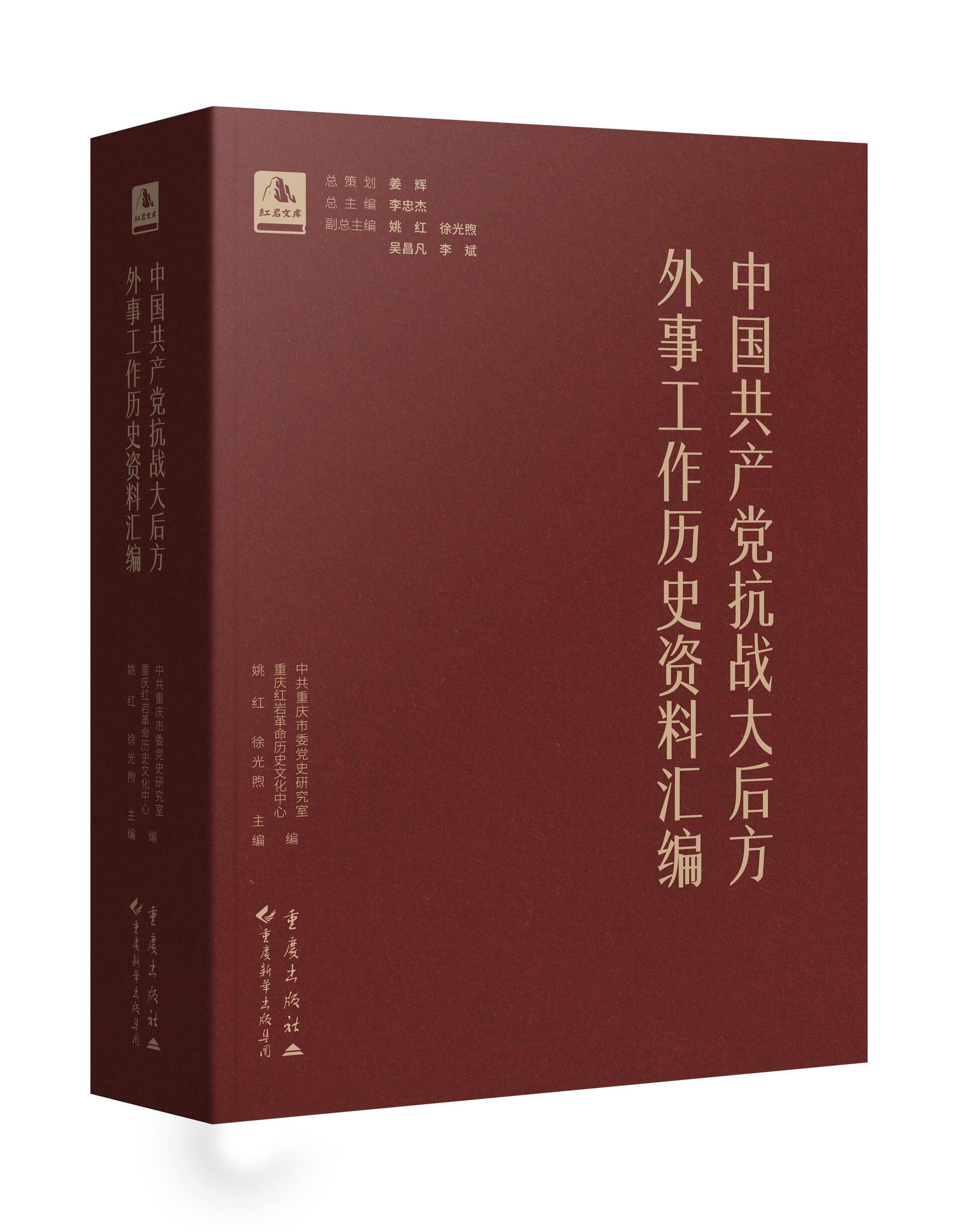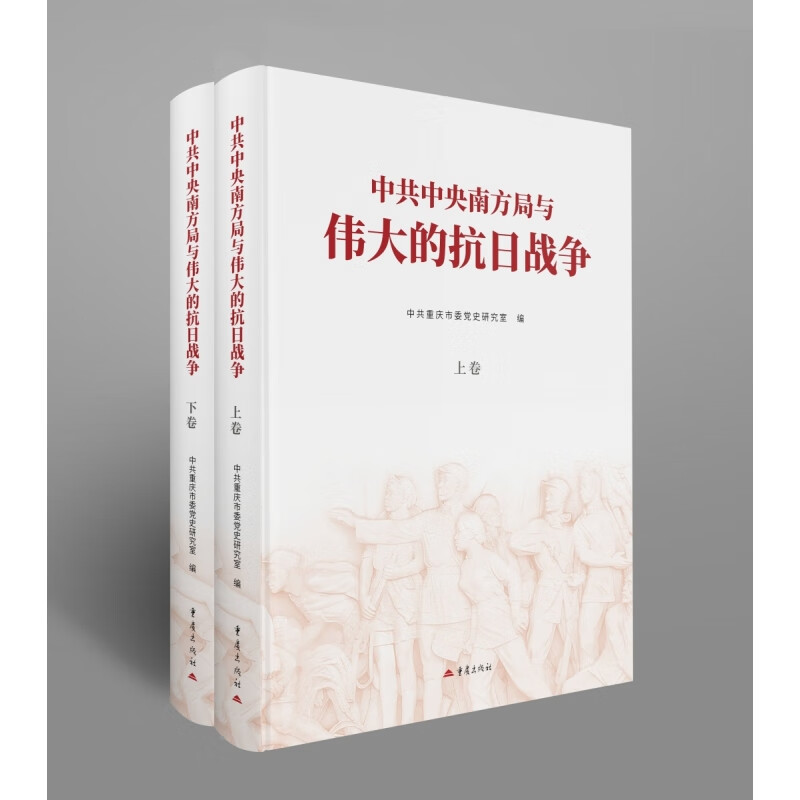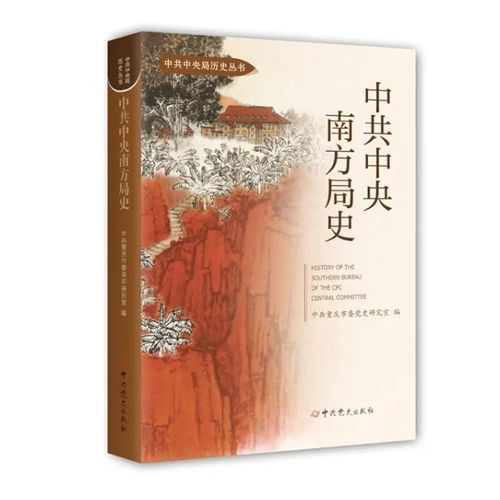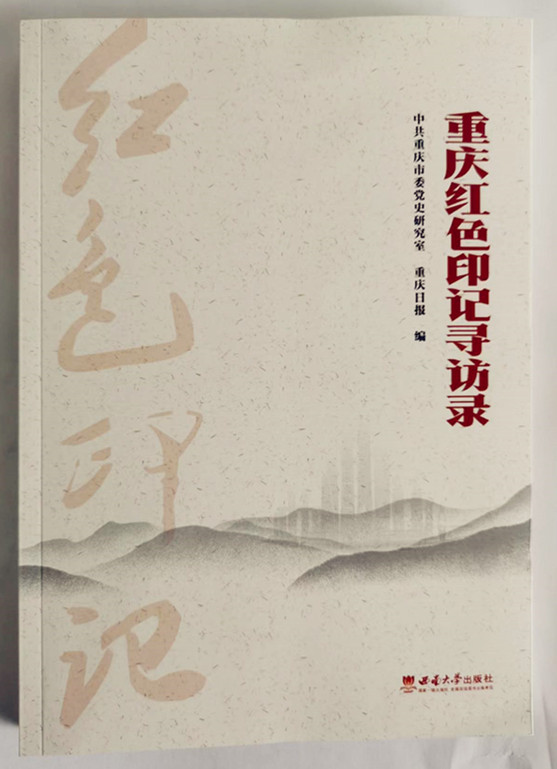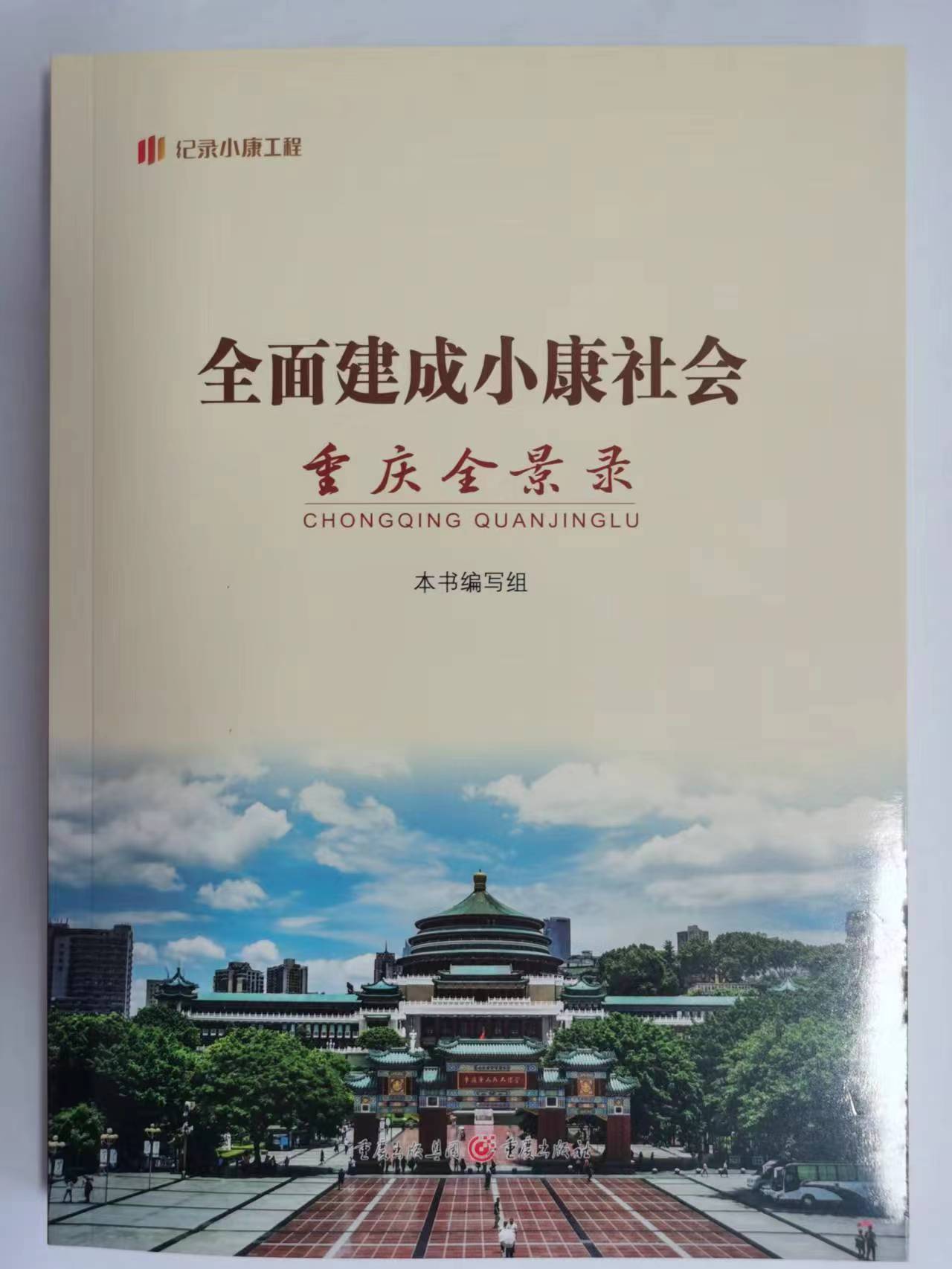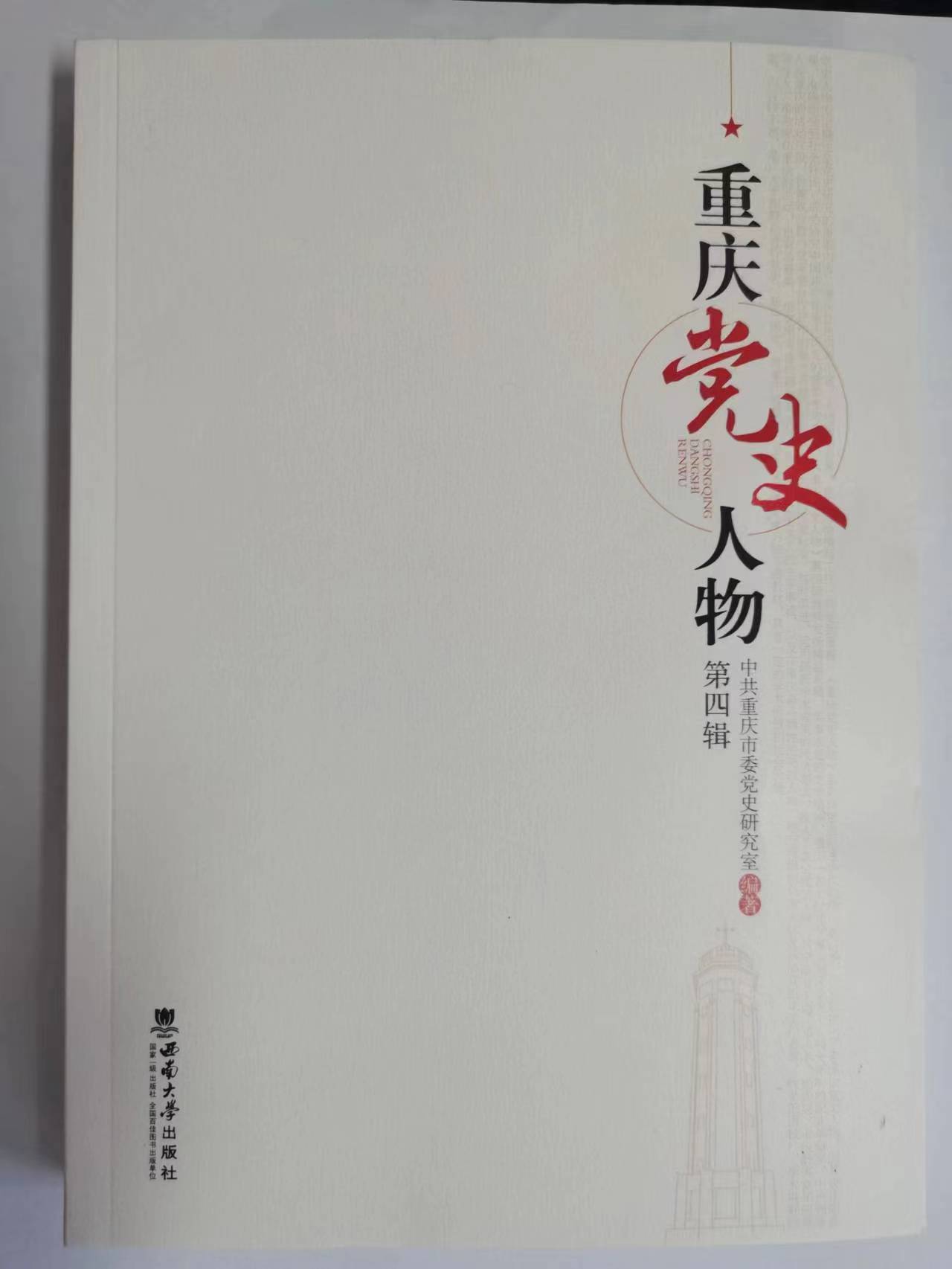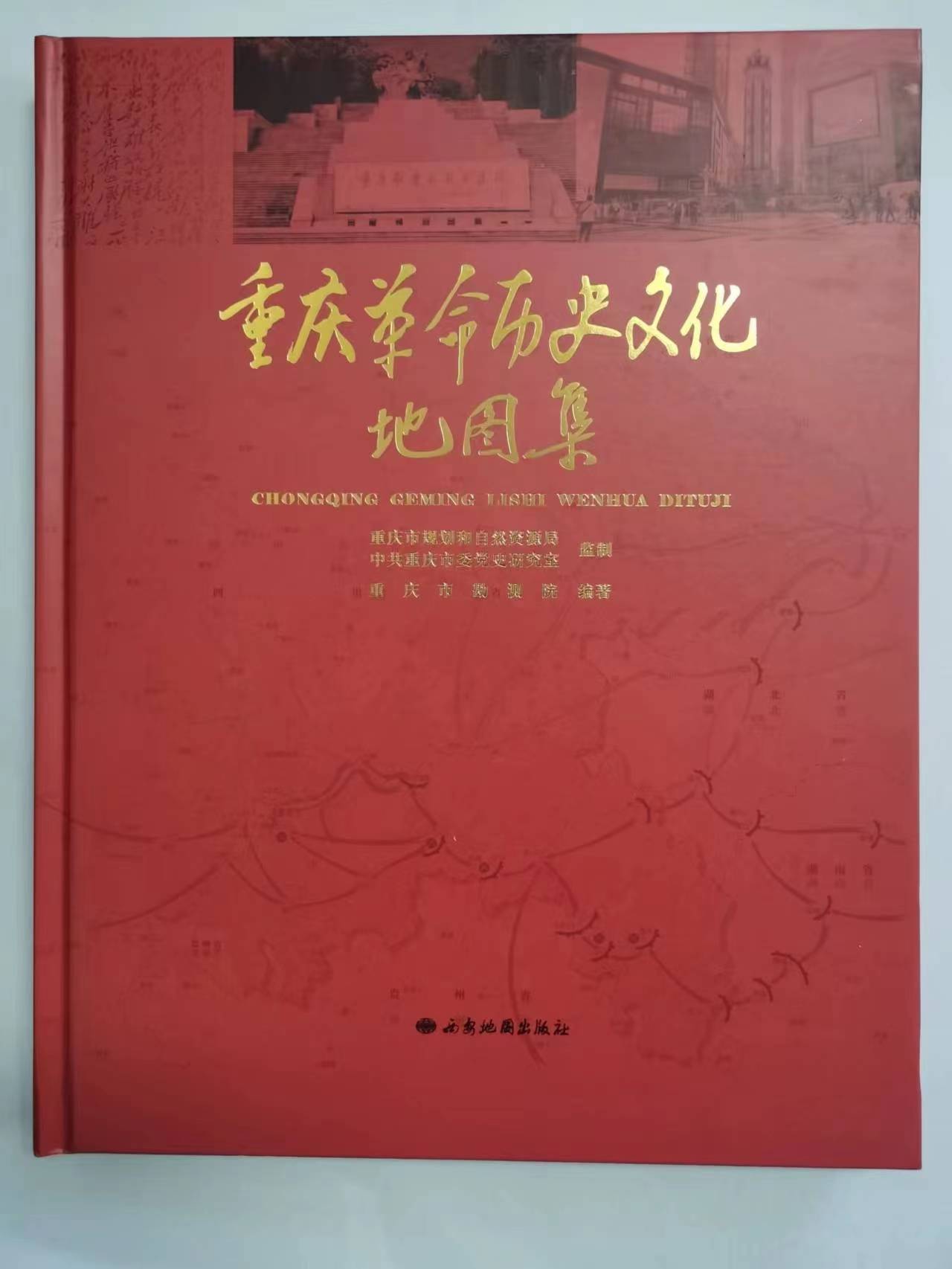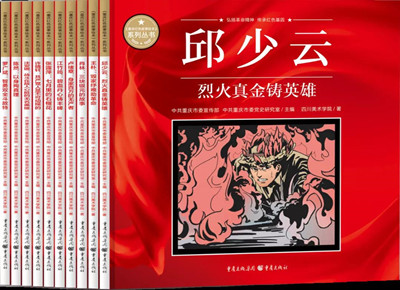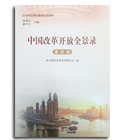冉启蕾
14年前的11月初,一封紧急寻找办《挺进报》时的收音机的求助信,转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的办公室。何事忠立即批示:“这台看似平常的收音机意义深远,影响重大,请涪陵迅速查找这台收音机的下落……”
来龙去脉
2006年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应邀到四川成都举办了一场以红岩魂为主题的展览。展览中,相关人员提到:重庆解放前夕,重庆的地下党在秘密开办《挺进报》时,使用过一台收音机,该收音机为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和前线战事以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现场只展出了收音机的图片而没有实物。
消息迅速传到因病未能前往参观的离休老干部林蔚青的耳朵里,当时已80多岁的林蔚青随即致电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是能找到收音机的原物,展览效果一定会比人工画的图片生动得多。”从那以后,林蔚青常常惦记着收音机的下落。
林蔚青与这台收音机有着特殊的感情。林蔚青是重庆人,新中国成立前系重庆电信局上清寺报房的报务员。他思想先进,曾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地下党领导人杨嘉平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办《挺进报》时所使用的收音机,即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提供给《挺进报》编辑室的。
2006年国庆节,林蔚青在成都武候祠南郊公园偶遇失去联系多年的老战友雷毅若。重庆解放前,雷毅若是地下党员,她和嫂嫂赖松经江竹筠介绍入党。雷毅若、赖松、易湘文等曾参与《挺进报》的发行工作。
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林蔚青即向雷毅若打听那台收音机的下落。雷毅若回忆: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遭国民党破坏而被迫停办。随后,她和赖松、易湘文等遵照组织安排,秘密转移到涪陵继续开展革命斗争,那台收音机和部分机密文件也被带到涪陵。重庆解放时,他们撤离涪陵,只将机密文件带到重庆交给了党组织,而那台收音机,听说有人移交给了涪陵地方党组织。
遗憾的是,赖松、易湘文已经辞世,而雷毅若对移交收音机的当事人和详细情况也记不清了,但她肯定收音机被带到了涪陵。
闻此消息,林蔚青激动不已,当晚便以“人民来信”的方式,给重庆市委宣传部写了封求助信,希望能在涪陵找到这台收音机。重庆市委宣传部领导立即对来信作出批示,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段描述。
艰难寻找
林蔚青老人的来信很快转到涪陵区委。涪陵区委非常重视,决定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委党史研究室承办,全力寻找。
当时,我担任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寻找收音机工作小组成立后,又担任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寻找呢?我们既不知道当年接收收音机的当事人,也不了解接收时的具体情况,只有查阅涪陵的档案,从中找到关于收音机的蛛丝马迹。我们查了几天,一无所获。
“发动群众一起找。”很快,我们通过当地的《巴渝都市报》、涪陵电视台、涪陵人民广播电台发岀号召,希望全区人民积极提供线索,一起寻找收音机。从2006年11月中旬开始,每隔三五天,工作小组便在媒体上公布一次寻找收音机的进度和过程。一时间,一场寻找收音机的活动,在涪陵地区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刚开始,线索不断。第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是收藏爱好者向汉明,他说:“涪陵刚解放时地方党组织还不够完善,收音机到底交给了谁没有具体线索,寻找起来难度很大。林蔚青老人说得有根有据,雷毅若老人也能肯定,那台收音机在他们撤离涪陵时交给了地方党组织,那收音机一定在涪陵。”向汉明表示,他会发动身边爱好收藏的涪陵人努力寻找收音机。
两天后,涪陵区国税局的韩先生给我打来电话,称他的父亲系原涪陵邮电局的职工,曾为中共地下党送过不少秘密文件。其父已于1969年去世,但生前多次给他讲过,重庆解放前夕,组织上将一批地下党员秘密转移到涪陵开展革命斗争,其间又从涪陵转移了一批人到万州。他的父亲为这些地下党员送过信,曾听说有台收音机被去万州的人带走了,估计那台收音机在万州。后经调查,此消息不确切。
11月16日,我们获得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涪陵一位离休老干部石德奎可能知道收音机的下落。随后,我立即找到了住在涪陵高笋塘干休所的石德奎。
1946年初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石德奎,曾任地下党涪陵县委组织部部长。据石德奎回忆,1948年3月,从重庆秘密转移到涪陵的雷毅若、赖松、易湘文等同志由他安排在我党相关部门工作,石德奎与他们打过多次交道,易湘文还将他们早前在重庆办的一大叠《挺进报》交给石德奎等人传阅。根据上级指示,石德奎将赖松的弟弟赖休成秘密安排到涪陵建成中学(今石龙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赖休成经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悄悄收听解放区和党中央的声音,第二天再把收听到的消息传达给石德奎和涪陵县委的主要领导及骨干同志。
两个月后的一天深夜,石德奎接到涪陵县委书记刘渝民下达的紧急任务,让他秘密将那台收音机和一大叠《挺进报》火速送到涪陵镇安镇大柏树村地下党员张光乾(系涪陵第三区区委书记)家隐藏。
第二天天未亮,石德奎将收音机和《挺进报》用旧衣服包好,再套上麻袋,装进一个大背篼。他打扮成农民,冒着大雨,躲过特务的盘查,经李渡、金银,走了30多里山路,中午抵达张光乾家。
石德奎告诉我们:“那台收音机不大,表面是木纹,上面有几个金属旋钮。当时我只知道收音机能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并不知道那是办《挺进报》的收音机。解放后过了两年,我碰见时任涪陵公安局长的张光乾,曾问起收音机的下落。张光乾说,当天晚上他和两个地下党员将东西藏在了屋后坟坝一个生基里,还对生基进行了伪装。”由于工作太忙,石德奎没再追问收音机的下落。
得到收音机的线索后,我们很兴奋,当即驱车赶往镇安镇大柏树村。然而,张光乾住过的房子,早在大跃进时期就拆了,生基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改成了梯田,毫无踪迹。张光乾于1972年去世,经过打听,我们在李渡老街找到了他的小儿子张献民。
张献民小时候听村里人讲,当年生产队挖生基改田时,挖到过一个宝贝。开始大家以为是特务埋的发报机,后来有人认岀是收音机,但并不知道它的来历。至于收音机的下落,一说是交给了省里,一说是有人送给了重庆的亲戚。
几天后,张光乾的堂弟张光玉主动向我们报料:“那台收音机是我大哥张光禄亲自背到涪陵,交给堂兄张光乾的。”据张光玉回忆,张光禄曾讲述把收音机背到涪陵后,看见张光乾将其交给两个陌生人。张光乾嘱咐两人要保管好收音机,找机会先上交到四川省,还说涪陵即将成立文化部门,到时再申请由文化部门使用。
收音机最终交给了谁,仍是个谜。由于当事人均已去世,也无档案记载,我们又反复查了几天,一无所获。
一波三折
据原涪陵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应全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期,四川省博物馆曾面向全省征集文物,尤其是革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文物,因此,涪陵将丰都县“太平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涪陵“二路红军游击队”的旗帜,罗云乡农民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长矛、大刀和土枪等,全部上交四川省博物馆。他推测,那台收音机也在那时被四川省博物馆征集。
王应全说:“1983年秋,涪陵市党史办召开会议,有几位老同志提到关于两台收音机的事。一台是由石德奎背到大柏树张光乾家藏匿的收音机,之后张光乾把它交给了涪陵县委,县委开会时还用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另一台收音机是解放初期从增福乡一位曾任国民党师长的家中没收而得。但没有依据证明收音机已上交四川省博物馆,只是一个估计。”
有了这一线索,我们决定前往四川省博物馆寻找。
2006年11月27日早晨,我们踏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到成都后,我们先到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收音机的下落,然后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由于该馆两次搬迁,损失了不少资料,均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第二天一早,我们忐忑不安地来到四川省博物馆。由于市政建设的需要,旧馆已完全拆除,新馆还未投入使用,只见旧博物馆的招待所变成了库房,临时办公室则是用简易材料搭成。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博物馆党委书记卢越立即组织相关负责人开会,强调寻找收音机的意义,要求全馆100多名职工全力配合,协助寻找。
有关人员在密密麻麻的档案登记资料中仔细查找“涪陵”“挺进报”“收音机”等关键词,11月29日下午6点,搜索结果出来了:《挺进报》的原件找到一部分,但没见到收音机。“会不会登记册上没有,而仓库里又有呢?”征得相关领导的同意后,我进入库房认真查找,仍
然无果。最后,文物保护部的张牧主任专门通知清理文物仓库的几位工作人员回忆,但没人见过收音机。
在成都寻找收音机期间,我们专程到天回镇成都老干部疗养院拜望了林蔚青。林老虽然年事已高,但耳聪目明,思路清晰。他动情地说:“万万没想到,重庆市委宣传部对一封群众来信这么重视,涪陵还专门成立工作小组认真寻找收音机的下落。我对那台收音机有特殊感情,是冒着生命危险将收音机提供给雷毅若、赖松、易湘文办《挺进报》的,如果能找到,红岩魂的展览就可以展出实物,有实物的展览会更加生动。如果最后仍然无法找到,我也没有怨言,谢谢重庆人民。”
在成都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们感动的事。《成都商报》记者张小军得知我们的意图后,说:“《挺进报》当时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有极大影响,那台收音机是立了大功的。我一定发动《成都商报》的记者一起寻找。”紧接着,张小军和一些记者跑了成都进仙桥、荷花池、武候祠一带的收藏品市场,但都没有发现收音机的踪迹。
回到重庆后,我们又到解放碑、沙坪坝、观音桥的古玩商店寻找,均无收获。
12月10日上午,重庆的一位黄女士给我打来电话,称她六天前在重庆三峡古玩城闲逛时,在二楼某文化艺术长廊看到一台老式收音机,上面贴着“陈然办《挺进报》时使用过的收音机”的纸条。闻此消息,我兴奋不已,立即赶往三峡古玩城,果然在里面见到了一台十分陈旧的老式收音机,但没有见到黄女士说的那张纸条。
我仔细查看了那台收音机,发现它产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无线电厂,显然不是我们要寻找的那台。
寻找办《挺进报》的收音机历时两个月,行程数千公里,接到各种报料和线索100多条,有数百人次参与了这次活动。尽管没有找到那台意义非凡的收音机,但重庆市委宣传部对涪陵寻找收音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相关领导说:“寻找办《挺进报》的收音机的整个过程,就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过程,也是对全市青少年进行红岩魂主题教育的过程,更是对红岩精神的一种宣传和体验。能找到,当然是好事,没能找到,但寻找的过程仍很有教育意义,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4年来,我从未停止寻找收音机的下落,寻找收音机工作小组尽管早已撤销,但我仍然惦记、牵挂着那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重庆解放作过贡献的收音机。如果红岩英烈泉下有知,肯定会为我们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到欣慰。
编辑/杨洋